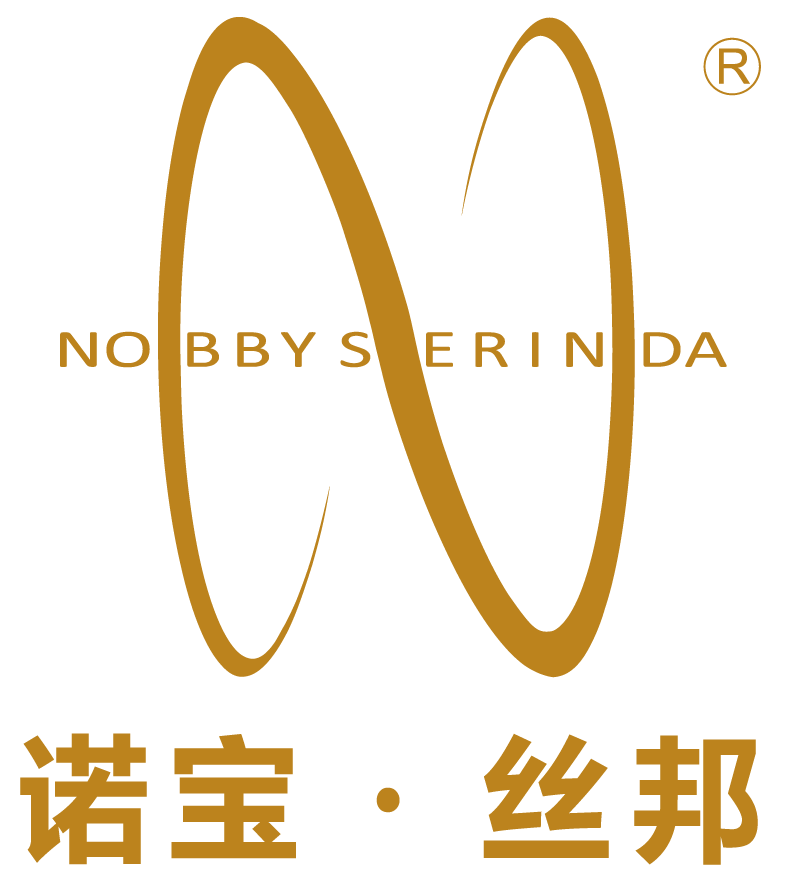
南方的冬天是悄没声儿地来的。没有冷风开道,没有霜雪报信,只是某一日清晨推窗,那扑面而来的空气忽然变了质地——像一块浸足了井水的软绸,凉津津的径直贴到人的脸上去。这时才恍然:冬,到底是来了。
这“冬意”是含混而迟疑的。看不见北国那样筋骨毕露的、苍褐的枝条,它们总还缀着些老绿,是榕树、香樟们舍不得褪去的旧袍子,边缘已显憔悴,却固执地守着最后一点体面。草地也没有全然枯黄,只在那一片沉郁的绿底子上,泛出些疲倦的淡黄,像褪了色的锦缎。阳光倒还是好的,明晃晃地照着,却没有多少暖意。人在这样的日头下走着,身上是亮的,骨头里却一丝一丝地渗着那无孔不入的湿冷。这冷,不是北方那种劈头盖脸的、爽利的干冷;它缠绵,带着水汽的阴柔,能透过最厚的棉衣,幽幽地钻进骨缝里,让你无处可躲。
然而这清冷寂寥的底子下,生命的律动却并未止息。墙角的蜡梅,偏在这时开了。花朵是蜜蜡黄的,半透明的,紧紧地抱着枝,香气却霸气得惊人,清冽冽、冷傲傲地荡开,能把周遭那一片昏沉的潮气都涤净了似的。还有水边那几株沉默的乌桕,叶子落尽了,却擎着一树一树珍珠白的籽,在灰蓝的天幕下,它们不说话,却比繁花喧嚣时,更显出骨骼的清奇与生命的韧劲。这南方的冬天,也最能试出人情的厚薄。屋里没有暖气,那湿冷是往骨髓里钻的。午后,若能觅得一片避风的墙角,让那淡淡的太阳晒着脊背,便是无上的享受。
从前在北方生活,见识过真正的寒冬。那是一种宣言式的、不容分说的冷。雪是干爽的,踩着咯吱作响;冷是锋利的,像薄刃刮过脸颊。万物肃杀,是一种大刀阔斧的、归于寂灭的壮美。而南国的冬,却总在“是”与“不是”之间徘徊。它冷得不彻底,绿得不鲜活,它冷的不够痛快,却也因此多了曲折和余韵。它让你在瑟缩中,更敏锐地察觉那一星腊梅的香,那一窗灯火的暖。它磨人的心性,也养人的情致。
夜深时,倘若下起雨来,那便是南方冬日的精髓了。雨脚细密,声音是沙沙的,悉悉索索的,不成节奏,却织成一张无边无际的、潮湿的网,将天地、屋舍、行人都温柔地罩在里头。枕着这样的雨声入眠,梦里也染着一层青莹莹的、润润的凉意。明早起来,石板路必是黑亮黑亮的,倒映着早起人伶仃的灯影;空气会冷得更加具体,也更加清新。这冬天,还要这样不紧不慢地、缠绵上许久。它或许终究酿不出一场酣畅的大雪,但它用这连绵的潮气与阴冷,耐心地浸泡着,渗透着,仿佛要将这片土地,连同其上栖息的人们,都淬炼出一种温润而坚韧的底色来。
南方的冬天,便是一位沉默的丹青手,不用皑皑白雪,只以淡淡的湿寒为墨,以不凋的苍绿为底,在天地间缓缓渲染着一幅气息绵长、意蕴深远的浅绛小品。
